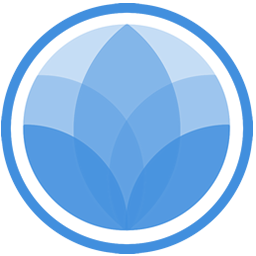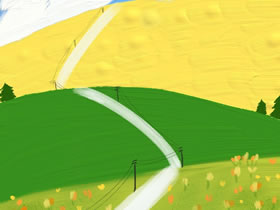特约撰稿人 黄晶(柏林,fantine2002@gmail.com)
V. Hösle先生是美国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德语及俄语文学系Paul Kimball讲席教授。他同时也兼任哲学及政治学两系的教授,并于2009年起出任圣母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在过去的30年间,他出版了35种著作,其中《黑格尔的体系》(Hegels System)、《道德与政治》(Moral und Politik)与《哲学对话录》(Der philosophische Dialog)等书尤为知名。
生平
1. Hösle教授,您能否向我们简略介绍一下您的生平、求学经历及研究兴趣?
自传性的评述常常显得自命不凡,但它们却能帮助他人理解一个哲学家的潜在动机,因此或许有其合理性。我于1960年出生于意大利米兰;我的母亲是意大利人,父亲则是讲授罗曼语文学的德国教授。我们在家中使用意大利语交流——比起真正的德国人,我们更像是一个意大利家庭,生活在德国却寻找每一个机会返回意大利。在6岁时,我费力地学习德语,并觉得自身始终更具有意大利人的特质。
当我从人文中学(Humanistisches Gymnasium)毕业时,我的年纪尚不到17岁。人文中学给予了我严格而优质的教育:从五年级起,我们便每日学习拉丁语;11岁时,我开始自修古希腊语。1977年秋季我进入Regensburg大学学习,并最终在21岁时于图宾根大学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波鸿和弗莱堡也曾是我的求学之地——当时德国教育系统的优势在于学费全免且学分极易转移;所以你能在许多地方学习并熟悉不同的学派。而讲授课(Vorlesung)的制度也十分卓越,你能从中获得对一位专家在某一特定领域的知识的概观,此外还无须写作论文,所以你仅仅需要吸收与消化。我的主修专业始终是哲学,而辅修专业由最初的科学史和拉丁文变为古希腊语和梵文。那时的德国大学仍是一个求知的天堂,而我则有幸在一些最杰出的学者那里学习。
在求学期间,我的兴趣主要集中于柏拉图与黑格尔。我被他们之间的相似与差异所吸引,同时,哲学史是否并不仅仅是相互冲突的诸多观点的汇聚这一问题也困扰着我。我的博士论文——也即我的第一部书——《真理与历史》(Wahrheit und Geschichte, 1984)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筹划了一种哲学史的哲学,而后半部则用这一理论来处理古代哲学从巴门尼德到柏拉图的发展。我将巴门尼德、阿那克萨戈拉与智者分别对应于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与现代启蒙运动,而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哲学则被我视为重建伦理学以及关于理性形而上学的尝试,它们展现出与康德哲学及德意志观念论的许多相似之处。我试图将黑格尔哲学史讲义所体现的系统进路与新的纂史知识结合,在我的第二本书《悲剧在索福克勒斯晚期作品中的完成》(Die Vollendung der Tragödie im Spätwerk des Sophokles, 1984)中,我提供了一个由黑格尔美学所激发的对希腊悲剧之发展的解释。多年后,我再次回到上述两个主题:在《解释柏拉图》(Platon interpretieren, 2004)这部文集以及研究哲学对话录文类的专著《哲学对话录》(Der philosophische Dialog, 2006)中我回到了柏拉图,而在《希腊三大悲剧家之级序》(Die Rangordnung der drei griechischen Tragiker, 2009)这部专著中则回到了悲剧家。
2. 在一开始,您谈到了您家庭的意大利背景。我感兴趣的是,您是否也受惠于意大利的思想传统?它与德意志传统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您能否谈谈意大利学术界的现状?
伟大的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曾举出四位对他影响最大的作者——我自己也将维柯视为在柏拉图和黑格尔之外对我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作者。我有幸与Christoph Jermann一同将他的代表作第一次完整地呈现给德语读者。 他教会了我将朝向法权国家(Rechtsstaat)的缓慢发展按照其内在的逻辑来加以理解。另一位伟大的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绝非仅仅作为一个对立面而对我产生吸引力:尽管他对道德与政治的分割是不可接受的,但权力具有其自身的逻辑,我在《道德与政治》第五章中对此加以探究,正是在这里我不断回溯到马基雅维利。我所最喜爱的第三位意大利作家当然是但丁,在一篇更长的文章中我比较了《神曲》和歌德的《浮士德》——它们或许是基督教欧洲最伟大的诗作。
与德意志人文科学传统相比,意大利传统更以经验为导向,因而缺乏前者所拥有的理论根基;维柯本人对于人文科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奠基的兴趣也远不及黑格尔。克罗齐尽管身为一名重要的人文学者,却是一个糟糕的哲学家;遗憾的是,在他之后,意大利的学院哲学主要以哲学史,而不再以系统为指向。与德国大学相比,意大利的大学甚至处于更为恶劣的状态之中,它们不仅资金短缺,并且也缺乏对绩效公平的保证。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拥有欧洲最古老大学的国家毁掉了自己的大学。
3. 您还谈到了在Regensburg所上的人文中学。而如今您的孩子在美国上私立学校,这些私立学校所提供的教育与您所受的人文中学的教育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吗?您觉得各自的优劣在哪里?
我还属于那种10岁便开始每天跟优秀的老师学习一个小时拉丁语的特权阶层;根据学校的安排,在四年后我们才会开始希腊语的学习,但我自己11岁时便已经开始自学希腊语。如今,人文中学的伟大传统即便是在德国本国也仅以一种退化的形式存在,在美国则从未有过同类中学系统(尽管在耶稣会学校中有其初级形式,但他们极少教授希腊语)。令我痛心的是,我的孩子不得不比我当年推迟两年才开始学习拉丁语,并且是在一所私立学校,因为这里的公立学校并不提供拉丁语教学。不过,我必须承认,美国学校确保了一种更大的社会活动性;而传统的拣选则大多由父母的教育背景所决定,这当然是不公平的。在这一意义上,为社会正义之故,我接受我的孩子所受的质量下降的教育。
4. 您在大学所学的三个专业分别是哲学、古典语文学和印度学(Indologie),您为何会选择这样一种组合?您决定学习印度学是因为它与您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有什么紧密的关联吗?
这一选择并不容易,因为我的兴趣非常广泛。选择古典语文学是因为我很好地掌握了古代语言;而印度学之所以吸引我,则是因为我希望了解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化。这一兴趣大概也解释了我后来为何会娶一位韩国妻子。对于异文化的学习无疑帮助我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内考察欧洲文化,并看到其界限。
5. 您先后游历了好几所大学,也曾追随许多老师学习,其中最为您推崇的是哪些学者?
我的哲学老师包括Franz von Kutschera、Hans Krämer和Dieter Wandschneider,Kutschera是一位非常广博的分析哲学家,而Krämer不仅奠定了新的柏拉图阐释,并且提供了一种严格的解释学理论,Wandschneider作为一位杰出的黑格尔研究者写有质量极高的黑格尔逻辑学与自然哲学论著,并将自然与技术哲学的传统带入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哲学上对我产生影响的师长还有Klaus Düsing和Werner Beierwaltes,前者是一位专注的康德研究者和德意志观念论史家,后者则由于阐释新柏拉图主义及其对德意志观念论的影响而闻名。此外,我还有机会师从机智而极富原创性的数学史家Imre Tóth,全面的中古神学史家Charles Lohr,著名的宪法学者和法哲学家Ernst Böckenförde,以及与Krämer共同创立了图宾根学派的古典语文学家Konrad Gaiser,而迄今为止我曾遇到过的最伟大的学者则是梵文学家Paul Thieme。
6.您刚刚谈到,著名的希腊哲学研究者Konrad Gaiser也是您的老师之一,我很想知道,他作为古典学者是否以一种与Krämer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您的学术道路,如果是,这一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黑格尔专家Wandschneider是我博士论文的导师,而Krämer则是这篇论文的第二评议人。作为语文学家,Krämer与Gaiser的责任在于确保我对于古代哲学的解释在语文学上是可靠的,即便这一解释是以黑格尔精神为导向的。他们两人均向我指明了如何有意义地解释柏拉图,不同的是,Krämer的兴趣偏向于柏拉图哲学的奠基结构(Begründungsstruktur),而Gaiser则对对话录的艺术形式更感兴趣——而要正确理解既是哲学家又是诗人的柏拉图,二者均是必需的。
7. 您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您近年来与McDowell和Brandom关于对德意志观念论阐释问题的讨论也尤其令人关注。您是否也受到了英美哲学的影响?
在进入大学之初,我所师从的是分析哲学家Kutschera,但遗憾的是,此后分析哲学长久被我忽视。然而今天我却将一些分析哲学的著作视为不可或缺的质量标准——我所推崇的分析哲学家包括Moore、Ryle、Hare、Strawson、Quine、Chisholm、Kim、Plantinga、Chalmers、Rawls、Kripke以及Searle。事实上特别有趣的一个问题是:Sellars、Brandom和McDowell如何再次走向了一种客观观念论(einen objektiven Idealismus)。
8. 您为何决定接受圣母大学的教职,并在此地继续您的研究和传播您的学说?
我的第一个终身教授的职位是在美国,但不久我便返回了德国,因为我感到自身与德意志文化紧密相系。然而此后在德国的经历整体而言令我沮丧:太多不合格的学生,教授的成果无人审核,政府部门的荒谬规定,还有德意志民族普遍的文化衰退。在圣母大学我第一次感到如此的自在,我终于能想象在此地度过我的一生。当然,我对于新的经验始终是敞开的!
哲学
1. 您曾说过,您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视为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四位思想家。您能否谈谈这一断言的理由?
广度与深度极少相互关联,但在这四位思想家身上,我们却看到了二者的结合——他们不仅跨越几乎一切哲学领域,并且在精确地论证他们的命题时带来巨大的革新性。
2. 在上述四位哲学家当中,您认为黑格尔和柏拉图甚至更高一筹。关于这两位哲人,您也各写有一部作品——《黑格尔的体系》和《解释柏拉图》。您在什么意义上将柏拉图和黑格尔视为在哲学上胜过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呢?
柏拉图与在哲学上受惠于他的亚里士多德不同,他不仅是哲学家,还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因此,我判他获胜。黑格尔建构了一个整合诸多哲学科学的百科全书式的体系,而这一系统在康德那里仅仅初具雏形;康德并未真正领会人类精神的历史性,黑格尔则将这一重大的发现融入了他的哲学体系。不过,康德的论证常常更为严格——重构黑格尔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但令人获益良多。
3. 我们刚刚谈到的这四位哲学家当中,两位是希腊人,两位是德国人。您的研究的一个特点正是将德意志古典哲学与希腊哲学相联系。在您看来,这一连接的合法性何在?
在1800年左右,德意志文化开始将自身理解为希腊文化的一种新的显像形式——德意志观念论依据时代的要求推进了柏拉图哲学,希腊艺术则启发了德意志的建筑与诗歌,而德意志古典语文学也取得了世界最高成就。然而,今天这一切几乎已不再留存。但我相信:柏拉图的客观观念论在1800年前后为何能通过谢林和黑格尔在一个现代形式中再次显现,理解这一问题是极其重要的。这使得客观观念论革新的可能性再次出现。我想,我们大概不必寄希望于欧洲,但或许应当寄望于美国——或中国?
4. 柏拉图和黑格尔是您最喜爱的两位哲学家。您将他们的哲学均视为客观观念论,而且您自身同样发展出了一套类似的观念论体系,这显然与大多数当代哲学家持有的反形而上学或自然主义的立场不同,那么,您认为客观观念论对于当代哲学可能有何贡献?
客观观念论具有诸多优点:它不仅承认一种永久有效的德性法则(Sittengesetz),并且提供了一种关于人类心灵历史发展的理论;它认识到了经验论的弊病,但又避免了像建构主义(Konstruktivismus)那样宣称:我们的概念建构会让我们与现实相分离;它坚持心灵的不可化约性,但也不否认其乃是自然的一部分,因为按照这一理论,自然的目的正在于心灵的创生。
5. 心灵哲学在今天已成为英美哲学的主流。客观观念论对于其中极受关注的身心问题提供了怎样的回答?
在我的对话录《Encephalius》当中,我为一种改良过的平行论做了辩护:我将一种伴生理论(Supervenienztheorie)与一种对自然发展的目的论解释相结合,根据这一解释,自然发展引发了必然与之在逻辑上相系的诸多心灵状态,即使它们伴生于各种物质状态。既然这一结果不能以演化论的方式(evolutionstheoretisch)得到解释,当我们拒绝互动论(Interaktionismus)时,我便假定,自然法则是以目的论的方式建构起来的——这就指向了创世信仰(Schöpfungsglauben)的一种形式。
6. 既然您自身的学说与黑格尔哲学紧密相系,我感兴趣的是,您如何评价分析哲学家例如Brandom和McDowell等人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新解释,据我所知,他们的解释也深刻影响了德国当下的黑格尔研究。这一连接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的独特进路有何问题?
在我看来,眼下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便是,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来重新表述传统的基本思想,尤其是伟大的系统哲学家黑格尔的思想——我因此为黑格尔主义与美国分析哲学的融合感到极为欣慰。所谓大陆与分析的对立并不恰当,只有好/坏哲学的对立。我认为Brandom与McDowell的主要问题是,他们未能创造性地汲取黑格尔概念生成(Begriffserzeugung)的方法, 也即辩证法。在他们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对概念生成这一问题的关注,他们的研究就整体而言是形式主义的,而未能澄清心灵在历史中具体的显现。
7. 关于英美哲学家对于德意志传统的重建,我们已经谈了很多。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德语世界。在德国当代哲学家当中,中国学界相对熟悉的只有哈贝马斯和Dieter Henrich。您能否越出他们之外,谈谈德国哲学的重要趋势?眼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德语作者和作品?
不再有世界知名的哲学家产生,这确实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特点。这既与创造力的普遍衰退,也与接受过程的扩散性相关——哲学家实在太多了,而种种学说的有效性要获得承认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我看来,Kutschera是德国最为广博的分析哲学家,Hermann Schmitz是极有趣的现象学家,Manfred Wetzel则是一位深刻的系统思想家。而在那些曾尝试重构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者当中,我始终觉得Dieter Wandschneider尤其具有原创性,因为他揭示了黑格尔自然哲学的不可扬弃并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重构尝试。
8. 百科全书哲学家(Universalphilosophen)的理想在德国具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卡西尔及布鲁门伯格等均属此列,然而德国哲学界年轻一代似乎开始转向膜拜新的“论证文化(Argumentationskultur)”(Dieter Henrich语)。您认为,这一新趋势对于德国哲学有何利弊?
我之前所谈的内容已经蕴含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伟大的哲学既是全面的,在论证上又不失敏锐。二者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今天,人们更加致力于精确性,这很好,但当对整体的通观丧失时,哲学的专门化将会阻碍创造性:因为论证只有在一个整体当中才能发挥效用。
9. 从您的研究,例如《哲学对话录》这部专著当中,我们了解到,在您看来,论证对于哲学而言尽管十分关键,但哲学绝非仅限于此,文学要素在哲学话语中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样我们现在便面对文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您能否谈一下您对这一关系的理解?
黑格尔美学提供的最具效力的洞见之一便是,艺术具有一个真理宣称(truth claim),但它并非普通的真理宣称:吊诡的是,正是艺术的虚构本质使得它比哲学更早地把握住真理。我对于文学的兴趣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它有助于澄清伦理和政治问题—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比方说,便是一座储存着大量政治洞见的宝库,因此它们常常出现在我的《道德与政治》(Moral und Politik)一书当中。其次,我还关注于如何拓展各种艺术形式的范畴,尤其是悲剧性和喜剧性这类普遍概念(参看我的专著《伍迪•艾伦》(Woody Allen, 2007))。最后,在过去的数年间我采用不同的文学形式来表达我的思想——例如讨论身心问题的对话录《Encephalius》,针对伟大的哥伦比亚“反动派”Gómez Dávila所写的反-格言录 ,以及讽刺短文《后现代的申辩》(Apologie der Postmoderne)。这一文学尝试开始于《哲学家的咖啡馆》(Das Café der toten Philosophen, 1996)这部已经被翻译为13种语言的书 ,书中收录了我与一个小姑娘之间真实的通信。我们在信中虚构了在哲学家咖啡馆中进行的对话,尽管这些通信的真实性被许多书评作者质疑,但其中最美丽的构想确实总是来自于小姑娘Nora。
10. 正如您刚才谈到的,您的哲学写作采用了多元的文学形式。除了您所谈及的文学本身所蕴含的哲学维度,当您关注哲学的文学形式时,是否也考虑到了接受的维度,即其与世界的关联?
康德区分了哲学的学院概念(Schulbegriff)与世界概念(Weltbegriff)。当哲学意欲作用于世界时,它便不能仅仅书写专业论著;它必须面向更广大的受众:既朝向其理智又朝向其心灵。因此,哲学必须复兴传统中存在的文学形式,正如启蒙时期的伟大思想家那样。
11. 由于列奥•施特劳斯及其学派的影响,中国许多柏拉图研究者也关注对话录的文学形式。您如何评价施特劳斯的柏拉图解释?
施特劳斯认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哲人出于对迫害的恐惧常常在他们的政治和宗教哲学中将一些观点隐藏起来,我觉得这一发现是有价值的。但希腊仅存在着很少的对渎神(Asebie)的迫害案例(目前被证实的仅有三例,即阿那克萨戈拉、苏格拉底与亚里士多德,渎神的指控只是一个托词,迫害者真实的意图是清除眼中钉或政敌的盟友)。柏拉图从不隐瞒他对于民主制的否定,他所隐瞒的乃是未成文学说,这一学说与政治毫无关涉。施特劳斯竟然宣称,柏拉图并不严肃对待他的理念学说,这在我看来无疑是荒谬的。
12. Hösle教授,您刚刚度过了50岁的生日。根据柏拉图的理论,您现在正处于一个哲学家生命的巅峰时期。您能否简略介绍一下您目前与未来的研究计划?
我正在为C. H. Beck出版社写作一部德国哲学简史。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之后,我对于德国哲学传统的特殊之处,也就是它和英法诸传统之间的区别很感兴趣。但我还有另一个长远的计划:我打算写一部客观-观念论解释学专著,所谓客观-观念论解释学即关于何为合法与非法解释的理论。这部作品的规范性立场将使之迥异于迦达默尔及其后现代追随者。
教化
1. 在《哲学家的咖啡馆》一书中,您涉及到了教育的诸多面相,此后您又写作了数篇文章讨论相关问题,并尝试进行教育实践。我们从中看到了教化(Bildung)这一特殊的德意志概念对于您的深刻影响,但由于教育体系的巨大变革,以塑造整全之人为目标的传统教化理念如今已经显得过时了。如果您觉得这一理念没有过时,那么它对于当下的意义何在?
正如歌德在《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中便已承认的,现代的成功正是基于专家(Fachmenschen)理念;但缺乏精神与教化的专家应为我们时代的诸多问题负责。想想环境问题——由此产生的后果之一便是,企业经济理性并不把作为整体的自然当作其思考的框架。真正的教化必须矫正专家主义(das Fachmenschentum);专家自身也必须融入知识之整体。
2. 自博洛尼亚法案实施以来,德国已经部分改用美国的高校体系。然而我们注意到,德国却并未接受通识教育的体制。您对美国的通识教育如何评价?这一制度是否有自身的缺陷,如果有,应该如何改进?德国未接受这一制度是否因为其不适用于德国,或者仅仅是这一改革考虑不周?
与德国大学相比,美国大学凭借其学院体系(Collegesystem)更接近于中世纪的大学理想:和德国的情况不同,在美国人们只能在四年的通识教育之后再进行医学或法律的学习。德国则没有这样的学院系统,因为德国中学此前部分地替代了这一系统。但遗憾的是,如今的中学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因此我担心,德国的教育系统很快就将显示出更多的缺陷。不过德国在外语学习这一个方面仍保持着优势,美国中小学与学院不可饶恕的错误在于忽视了外语教学——这自然也因为目前几乎每个受教育者都学过英语。
3. 您之前提到,您离开德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德国学生质量堪忧,您觉得今天的德国学生与您那一代的学生相比,差距主要在哪里?是什么造成了这一衰退?
在1968年之后,德国建立了很多新的大学,并且吸引了许多年轻人进入大学学习。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人们却未能同时成功地创造一个以绩效为基础的公正市场体系。大学学习在美国是一种投资,而在德国它却被当作一种生活形式提供给许多年轻人。此外,很多教授获得了同他们前辈同等的权利。然而,尽管这些权利对于那些有着极高阶层伦理的前辈而言曾有着积极意义,但对于这些后辈而言却过度而不合时宜了。
4. 2009年圣母大学成立了高等研究院(NDIAS),由您出任院长,而您主编的文集《一所天主教高等研究院的理念》(The Idea of a Catholic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也于今年出版。您能否在此简略谈谈何为一所天主教高等研究院之理念?圣母大学高研院与别的高研院相比有何特色?
圣母高研院在两个方面出类拔萃:与天主教传统相一致,我们不仅希望支持那种综合了规范性与描述性维度的研究,还希望能促进跨学科的项目。Verum–bonum–pulchrum(真、善、美)是我们研究院的铭文——善(bonum)将我们与著名的普林斯顿高研院标志相区别。希望中国学者也踊跃申请我们的项目!
5. 在圣母高研院委员会名单中不仅有神学、文学、哲学专业的教授,还有化学家和工程学家,在您看来这样一所研究院相对于各个独立院系的优势是什么?
在对于保证专业质量不可或缺的单个系科之外,大学还需要设立一些机构来处理那些只能借助于多种方法来解决的问题。未来的大学将拥有越来越多的此类研究跨专业问题的机构。
6. 我们谈了很多公共生活中的教育问题。最后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在私人生活中您是如何教育您的孩子的?您觉得对于孩子的成长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道德乃是我们的出发点——几乎没有别的作家能像狄更斯一样帮助我们塑造对此的感知,我已为我的孩子在晚间朗读了九部他的小说。就智性而言,我觉得重要的是,他们能理解自身出于好奇而希望了解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机械性地记忆。他们必须把握对世界历史的知识,以此作为统括其他知识的框架,而古代希腊与罗马则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基础——眼下我正每晚为他们朗读普鲁塔克。